而我懦弱順從的外殼之下,那顆被忽視、被委屈、被慢慢磨蝕的心,卻因為這四個字,劇烈地悸動了一下。
母親是知道些什麼嗎?還是僅僅基於我過去偶爾流露的抱怨,以及對周家一貫作風的了解,就在我可能最脆弱的時刻,給出了她認為最強有力的支持和退路?
掌心沁出冷汗,手機變得滑膩膩的。我幾乎是驚恐地鎖上螢幕,把它死死攥在手心,好像那是什麼燙手的違禁品。
心臟在胸腔里瘋狂擂鼓,撞擊著肋骨,聲音大得我懷疑周圍人都能聽見。血液一股腦湧上頭頂,又迅速褪去,留下陣陣眩暈。尾椎骨的疼痛變得遙遠,另一種更深沉、更尖銳的戰慄從脊椎蔓延開。
我強迫自己拿起筷子,伸向那盤已經沒什麼熱氣的青菜,手抖得厲害,菜葉差點掉在桌上。我匆忙塞進嘴裡,味同嚼蠟,根本嘗不出任何味道。
「婉晴是不是不舒服?臉色這麼白。」一位坐在斜對面的阿姨注意到了我的異常,關切地問。
刷的一下,好幾道目光聚焦在我臉上。
我像被捉住的賊,心臟猛地一縮。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:「沒…沒事,可能就是有點累,歇會兒就好。」
婆婆瞥了我一眼,語氣淡淡的:「懷孕是這樣的,嬌氣些。累了就早點回房歇著吧,這裡我們收拾。」
她的話聽起來像是關心,卻輕易地將我再次從「我們」中剔除了出去,並暗示了我的「嬌氣」和不合時宜。
若是往常,我大概會內心酸楚,然後默默接受這種安排,甚至還會有一絲愧疚,覺得自己確實不夠懂事,給忙亂的壽宴添了麻煩。
但此刻,母親那句話在我腦海里瘋狂迴蕩,像有了自己的生命。
「我們養得起。」
這個「我們」,是指我和她還有父親嗎?如此堅定,毫不猶豫。與我在這個家裡感受到的疏離和工具化,形成了慘烈得令人想發笑的對比。
周偉終於後知後覺地看過來,喝了酒的他眼神有些渙散:「不舒服?要不要喝點熱水?」語氣是程式化的,甚至沒等我回答,就又轉頭接上了他表弟的話茬。
看,這就是我的丈夫。我孩子的父親。
一瞬間,那股強烈的、幾乎要衝破胸膛的委屈和憤怒,竟然奇異地平復了一些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冰冷的、帶著一絲瘋狂滋味的清明。
我放下筷子,聲音平靜得出奇:「媽,那我先上去躺一會兒,實在撐不住了。」
「去吧去吧。」婆婆揮揮手,注意力已經回到了餐桌上。
公公點點頭,沒說話。
周偉「嗯」了一聲。
我扶著桌子邊緣,慢慢站起來。動作很慢,一方面是因為身體確實沉重不適,另一方面,我需要極力壓制住身體的顫抖。
我沒有再看任何人,低著頭,一步一步,儘可能地平穩地走出餐廳,走向樓梯。
身後,喧鬧聲再次響起,仿佛我這個人從未存在過。
爬上樓梯的每一步都異常艱難。身體沉重,心跳如雷。腦子裡亂糟糟的,母親的話和周家眾人的面孔交替閃現。
回到臥室,關上門,隔絕了樓下所有的聲音。世界瞬間安靜下來。
我背靠著冰冷的門板,緩緩滑坐到地上,終於不再壓抑,大口大口地喘著氣。眼淚毫無預兆地決堤而出, silent地洶湧流淌,打濕了衣襟。
我顫抖著,再次點亮手機螢幕。那行字還在。

去父留子。我們養得起劉悅。
這不是商量,不是詢問。這是一句宣告,一句來自母親的最堅實的堡壘搭建。
她一定是猜到了。猜到了我在這場婚姻里的處境,猜到了我在這個家庭里的位置,猜到了我此刻的狼狽和絕望。所以她給出了最極端也最徹底的選擇。
「去父」,意味著什麼?意味著和周偉離婚,意味著和我苦心經營了三年的婚姻徹底告別,意味著孩子一出生就將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父親。
這需要多大的勇氣?會面臨多少非議和困難?
可是,「留子」。我的孩子。我將擁有我的孩子,完全地擁有。而不是讓我的孩子,在這個明顯重男輕女、忽視母親感受的家庭里,重複我的壓抑,或者因為性別而遭受冷眼。
「我們養得起。」這是底氣,是退路,是來自原生家庭毫無保留的支持。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。
這個認知像一股暖流,注入我冰涼的四肢百骸。
可是……真的要走這一步嗎?周偉,他雖然遲鈍、自私、被父母影響深,但他真的壞到無可救藥嗎?我們之間,難道沒有一點真情了嗎?這個家,難道沒有絲毫值得留戀的地方嗎?
而且,離婚……孩子出生就沒有爸爸……我真的能做一個單親媽媽嗎?社會的眼光,未來的艱辛……
劇烈的心理掙扎撕扯著我。一邊是母親描繪的那條充滿未知但卻可能通向解脫的道路,一邊是眼下這條看得見盡頭、令人窒息卻看似「正常」的坦途。
我癱坐在地上,無聲地流淚,內心是兩個世界的激烈搏殺。樓下的歡笑聲隱約傳來,諷刺般地提醒著我現實的割裂。
我不知道坐了多久,直到眼淚流干,眼睛腫痛。情緒極度爆發後,是精疲力盡的虛無。
我掙扎著爬起來,走到窗邊。窗外月色很好,清冷地灑在地上。小區的路燈溫暖安靜。
一輛車駛入樓下停車位,車燈熄滅。司機下車,熟練地鎖車,然後快步走向某個單元門。那是一個回家的動作。
這裡是我的家嗎?這個裝修精美、物質不缺的房子?
曾經我以為是的。我懷著憧憬嫁進來,想經營一個溫暖的小家。但不知從何時起,我成了這個房子裡最忙碌的保姆、最透明的存在、最不被在意的附屬品。
我下意識地撫摸著高高隆起的腹部。肚子裡的小傢伙似乎感受到了母親劇烈的心緒起伏,不安地動了幾下。
一下,又一下,溫柔而有力的胎動。
像一個小小的拳頭,敲打在我的心上。
為了她/他?
我的孩子,難道要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嗎?看著母親委曲求全,看著父親漠不關心,看著爺爺奶奶或許因為性別而流露出的失望?
母親那句話再次清晰地響起。
「我們養得起劉悅。」
重點不是「去父」,甚至不是「留子」。重點是「我們養得起」。是這份無論我做出何種選擇,都被無條件接納和支持的底氣。
這一刻,一直盤踞在心頭的迷茫和恐懼,忽然被一種巨大的勇氣驅散了不少。
我深吸一口冰涼的夜空氣,拿起手機,給母親回了一條信息。
只有簡短的三個字。
「知道了。」
章節三:裂痕
壽宴後的日子,表面平靜,內里卻暗潮洶湧。
我依舊做飯、收拾家務,但不再像過去那樣拚命搶著干,生怕被說一句懶。我開始有意識地放緩節奏,累了就坐下歇歇,渴了就給自己倒杯溫水,而不是忍到所有事情忙完。
變化細微,但足以引起周家的不適。
「婉晴,這都幾點了,早飯還沒好?」第二天早上,婆婆看著桌上比往常晚了十分鐘出現的清粥小菜,語氣帶著明顯的不悅。
「媽,我有點腰酸,動作慢了點。」我平靜地回答,給自己也盛了一碗粥,拉開椅子坐下,準備一起吃。以前,我通常是站著或者忙別的,等他們都吃得差不多了才匆匆扒幾口。
公公和周偉已經吃上了,沒說話。周婷打著哈欠下樓,看到我也在桌上,愣了一下。
婆婆皺皺眉,似乎想說什麼,但最終只是嘀咕了一句:「懷孕就是事多。」便也坐下了。
餐桌上氣氛有些微妙的凝滯。沒有人給我夾菜,沒有人問我為什麼腰酸。周偉很快吃完,碗一推:「我上班去了。」
「嗯。」我應了一聲,沒有像往常一樣起身幫他拿包送他到門口。
他自己拿了公文包,換鞋出門。關門聲比平時響了一點。
我低頭,慢慢喝著自己的粥。母親的那條信息,像一顆種子,在我心裡發了芽。我開始用一種抽離的、審視的目光觀察這個家,觀察周偉。
我發現,他確實很少主動關心我。下班回家,第一件事是打開電視或刷手機。偶爾問我一句「孩子今天鬧沒鬧」,更像是一種程式化的任務。我提到的產檢細節、身體不適,他通常是左耳進右耳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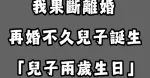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