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好……我會被悶死的。
失去意識的前一秒,我看到沈灼發了瘋似的朝我跑來。
「湘湘!」
他喊得撕心裂肺。
12
我醒來後,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裡。
我媽在幫我擦臉,力度和小時候沒什麼區別。
這麼多年我一直想問她,她到底是在幫我擦臉還是在揉面。
「媽媽……」我張了張口,嗓音嘶啞。
「囡囡。」我媽的動作一僵,眼淚就這麼落了下來。
醫生來檢查後,說我是窒息導致的昏迷,醒了以後配合做幾項檢查,再輸點液,很快就能出院了。
我環視四周,有了不祥的預感。
「沈灼呢?」
父母對視了一眼,吞吞吐吐:「小灼他……還在 ICU……」
……
歷時兩個多月的入室搶劫案終於告破。
拋開沈灼與宋巧這件事不論,在刑偵方面,他確實能力出眾。
連著好幾次都差點被抓住,劫匪被沈灼逼得走投無路,只能藏在下水道里,平時靠一些小偷小摸苟且偷生。
夥同另一名劫匪實施入室搶劫和強姦之前,他就已經背著命案。彼時也是他拿那人墊背才僥倖逃脫,他知道自己被抓住會坐很久的牢。
就在這時,他看到了獨自下班回家的我,想要故技重施搏一把,搶一筆錢之後遠走高飛。
卻沒想到被同樣加班到很晚的沈灼看到。
沈灼在搏鬥中逮捕了綁匪,胸口卻被連刺兩刀。
聞訊趕來的同事撥打了 120。
據說被推進手術室時,他還強撐著精神喃喃:「原來……你當時,這麼疼啊……」
同事吼著讓他不要睡,睡了就再也醒不過來了。
他最後一句話是:「如果、如果我沒出來……幫我告訴、告訴湘湘……我……」
沒有人知道他想說的是什麼。
手術做了一天一夜,主刀醫生說,沈灼很有可能變成植物人。
「湘湘,事已至此,你……還要退婚嗎?」
我媽小心翼翼地問我。
她心疼我,擔心我迫於道德壓力,重新接納沈灼。
我沉默了很久很久,最後說:「我等他醒來,再說。」
13
出院後,我去照顧沈灼。
倒也不是迫於道德壓力什麼的,他救我一命,我照顧他也是情理之中。
沈灼的父母期望我能對他說說話,可我望著渾身插滿管子的沈灼,張了張口,卻不知道說些什麼。
老兩口絕望之際甚至聽了婆子的話,跪下來求我,想提前辦婚禮沖喜。
被我爸媽罵回去了。
我媽把檢查報告單摔在他們面前,「夠了!我自己的女兒我心疼!想不顧我女兒的意願讓兩個孩子辦婚禮,沒門兒!」
門外的人在激烈爭執,門內,我替沈灼把臉擦乾淨,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說著話。
又或者是我在自言自語。
「今天是你昏迷的第五十天,醫生說你已經度過了危險期。」
「你瘦了很多,沈灼。」
他的眼下有淡淡的烏青,原本的臉頰肉已經消失了。
冰冷的消毒水汽味鑽入鼻腔,我坐在他的枕邊,注視著那張讓我愛過也恨過的臉,如今只剩下蒼白和沉寂。
「門外很吵是不是?這也難怪,因為你還在昏迷,二老的頭髮白了一半,他們都是唯物主義者,現在卻信一些神神鬼鬼的東西。可是為人子女,我卻沒辦法指責他們,所以我只能在你這兒躲一躲,但是話說在前面,我不同意沖喜。」
沈灼沒有回應我。
我沉默了很久很久,久到門外的聲音消失。
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空寂的病房內響起:「不僅如此,我還是想要退婚,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冷漠?明明你救了我來著……現在說這種話,聽上去簡直不是人。」
沈灼靜靜地躺在那裡,只有心電圖的聲音證明他還活著。
那平穩的線條像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,又像是達摩克利斯之劍,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落下。
「可是沈灼,我嘗試過說服自己了。」
「說服自己答應沖喜,說服自己留下來,陪在你身邊一輩子。可是我真的很害怕,我怕你再也醒不過來,我更怕自己變成一個狼心狗肺的東西,怕我歲月漸長,對著你這張臉,怨懟你為什麼要救我,把我困在一個恩情織就的牢籠里翻不了身。」
我忘不了曾經的痛苦。
可是現在,連恨都成了奢侈。
我沒辦法愛他,也沒辦法繼續恨他。
「沈灼啊……我情願躺在這裡的人是我。」
細細密密的絲線勒緊我的心臟,讓我透不過氣來。
良久,我擦了擦腮邊的淚,強笑道:「最近也不知道怎麼了,我經常夢見你,我都想好了,假如,我是說假如,你醒不?ù?過來的話,你的父母,我會替你養,就當我欠你一條命。」
我吸了吸鼻子,眼眶發酸。
「我不怪你了,沈灼。」
「新的一年快到了,你快點醒過來吧。」
「我求你……」
此時,儀器發出尖銳的響。
「好。」
他的眼睛閉著,眼角划過???一滴淚,嗓音低啞:「我們……退婚。」
14
沈灼到底是傷了身體,再也不能從事強度太大的工作,被調到相對清閒的文職部門。
對他這樣一個從小就立志要成為刑警的人來說,是毀天滅地的打擊。
更別提,因為傷口靠近心臟,日後的下雨天,他都會很難挨。
我們退婚後,房子留給了我,車子給了他。簽署協議的那天我們相顧無言,他紅著眼眶看著我,像是要把我刻在心底。
「以後什麼打算?」
我給他看手機上的紅頭,「我要去 Y 國學習了。」
Y 國廣播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新聞媒體,老領導由於身體原因退居幕後,台里考察後派我去進修,回來後會晉升播音總主任。
他把簽好的協議遞給我時,手抖得合了好幾次筆蓋。
而我喝了一口咖啡,望著門外陰沉的天。
「雨天路滑,你路上小心。」
成年人的告別往往就是這樣。
體面、溫柔,且決絕。
再後來,隨著資歷的增長,我換了很多很多男友,每個都不超過 25 歲。
他們或真心或假意,有的想從我手裡撬更多的資源,有的陷進去了,想同我結婚。
我從來都是置之一笑,然後給一筆可觀的分手費。
因為我發現,新鮮的關係比穩定的婚姻好很多。
我在世界多地都購置了房產,各種大獎拿到手軟,名利雙收,是媒體口中的「新聞女王」。
父母偶爾會頭疼我的終身大事,這個時候我就送他們去世界各地旅遊。二人見多了世面,也就不受傳統觀念約束了,覺得我開心就好。
情人節的時候,F 市罕見地下了雪。
新男友興致勃勃地約我去遊樂場,中途又神神秘秘地離開。
我在廣場中心等他的時候,被一個穿著大衣的人吸引了注意。
他的身材修長,下頜線鋒利,面容如以前一般俊朗。見到我,他愣了一下,打了個招呼。
「好久不見。」
「好久不見。」
新男友跑過來,手裡拿著兩張摩天輪的票,見到我在同他說話,沒敢過來打擾。
沈灼望著他手裡的票,眸子裡划過一絲黯然,朝我扯出一個笑意,「那我先走了。」
「嗯。」
他轉身走了,分明正值壯年,卻步履趔趄。
腦海里不合時宜地想起一句話:有些人故地重遊,是為了刻舟求劍。
他的身影消失在雪裡,新男友在一旁插科打諢,想要同我去坐摩天輪。
我看出他的心思,搖搖頭,笑著對他說:「你自己去吧,我畏高,在下面等你。」
遊樂園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傳說,抑或者說,刺激消費的手段。
據說情人節這天,情侶在摩天輪登頂時擁吻,就會長長久久。
十年前,我自己已經坐過一次摩天輪。
今後,不可能再坐了。
【全文完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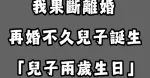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